|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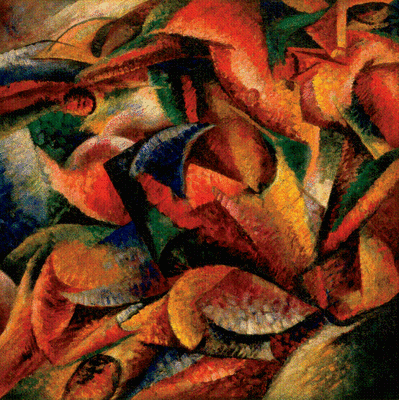
烏姆伯托•波西尼、《人體的活力》、1913、布面油畫、97×97厘米。
沿著這條路,經(jīng)過幾條街區(qū),就是Palazzo Reale, 這里展出了250多件作品,由吉奧瓦尼?利斯塔(Giovanni Lista)和埃達?瑪索羅(Ada Masoero) 策劃。展覽的重點是這場運動的風格化發(fā)展,通過塑形活力從新印象畫派的源頭(也是它最為知名的一段時期)到20年代的“機械藝術”和30年代的“動感繪畫”。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唯一一個沿著傳統(tǒng)的藝術史鏈條發(fā)展的百年展,歷史本身就是必不可少的風格。展覽無所不包的特點,囊括了那些不太為人知的作品,如安里科?普蘭波利尼(Enrico Prampolini)的全集(未來主義的第二代),但是,這種特點也使得展覽變得松散而不集中。當然,松散也不是壞事,因為可以引入嶄新的敘述方式,不過,這場展覽并未做到這一點。
它以兩個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進行了終結:對于戰(zhàn)后時期未來主義遺產進行了簡短的總結,一間小放映廳里,觀眾們可以看到一些非常不錯而又很難看到的未來主義以及與之相關的電影資料,有蒂娜?科德羅(Tina Cordero),吉多?馬蒂納(Guido Martina), 皮坡?奧里阿尼(Pippo Oriani)的Velocità(1930), 還有很多紀念意大利現(xiàn)代化的紀錄片。部分是由于受到未來主義詩意性以及蘇聯(lián)電影創(chuàng)作的影響,這些影片都是由Istituto Luce制作,在三十年代是納粹的宣傳機構。那么,提起這番瓜葛,《未來主義1909-2009》是唯一從時間上講述未來主義發(fā)展的作品,而在展廳里,任何關于這場運動在二三十年代與法西斯主義有關的討論都幾乎缺席。關于這場沉默,可以說,Palazzo Reale不是唯一。也許,這一話題和百年展的慶典調調并不相符。或者說,關于這場運動與法西斯之間關系的歷史性缺失、過于簡單化與如今意大利右翼突然對未來主義報之以熱情的接受,將其作為文化右派的美學表達有所關系?
“未來主義回到了米蘭,”墻上的一篇文章這樣宣布道,“這里是它的發(fā)祥地,在早期和那些有意思的日子里,這里是運動的地點。”這沒錯,但是,蓬皮杜中心舉辦的展覽《巴黎的未來主義-先鋒大爆炸》卻給了它一擊。展覽由迪迪耶?歐登杰(Didier Ottinger)和埃斯特?科恩(Ester Coen)以及馬修?吉爾(Matthew Gale)策劃,開啟了2008年10月的慶典活動,每個人都參與進來。
蓬皮杜展覽的野心是將未來主義的起源在前前后后的起伏中定位,這場運動發(fā)生在巴黎,有意大利的畫家,還有他們的同行們,不僅包括畢加索,布拉克,沙龍立體主義者們,還包括俄羅斯立體-未來主義者們,英國的漩渦派畫家,它將1912年2月未來主義在巴黎Bernheim-Jeune畫廊開拓性的展覽重建,將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作品匯集在了一起。同時,它也努力將一場超越民族界限的運動發(fā)展進行定位,突出了巴黎作為各國藝術家云集地和這場運動發(fā)祥地的重要地位,而法語作為共同的語言,使得這種交流得以產生。從這個意義上講,展覽對于巴黎未來主義的否定與同化,意味著從一開始,這場運動就是一場國際性而非嚴格意義上的民族性的運動。另一方面,它對法國在未來主義上的鏈條重新進行了歸攏。
當展覽來到了羅馬的Scuderie del Quirinale時,它的委托人變成了科恩, 她將未來主義帶回了家。對展覽重新進行了修正,盡管保留了Bernheim-Jeune展覽的大部分畫作,廣泛的主題性分組代替了歷史性的重構。展覽的前半部分,全都是意大利的油畫和雕塑。只有先確定意大利的重要地位后,關于未來主義在國際上的傳播這樣的議題才可以被提及。在展覽的第二半部分,科恩減少了沙龍立體主義的畫作,法國未來主義者菲利克斯?戴爾?馬勒(Felix Del Marle)只有一幅畫被包含進去,而蓬皮杜展覽中,他的畫占據(jù)了半個展廳。在Scuderie,從美學上講,最令人震撼的要屬塞維里尼(Severini)和畢加索帖紙畫了,以及阿爾登格索菲奇(Ardengo Soffici)和柳波夫?波波娃(Liubov Popova)的小油畫。對面,是巴拉(Balla)的三幅抽象作品,標志著未來主義向前的發(fā)展;在最后的這些作品中,未來主義最終擺脫了死氣沉沉、阻礙其發(fā)展的圖形表現(xiàn)手法。
有趣的是,泛歐洲的現(xiàn)代主義和先鋒運動全景圖,成為了科恩在羅維雷托的MART獨立策劃的展覽《未來主義宣言100×100:100周年/100次宣言》的中心主題。在所有的百年展中,MART展可以說是最大膽無畏的展覽,它突出了一戰(zhàn)前夕先鋒創(chuàng)作的國際精神,將表現(xiàn)主義者、立體主義者、抽象畫家都匯集到了赫爾瓦特?瓦爾登(Herwarth Walden)的柏林周刊Der Sturm(成立于1910年),還有俄羅斯的原始主義者,立體未來主義者,光線主義者。與傳統(tǒng)畫冊不同的是,展覽的出版物是一本書,記錄了米蘭之外的未來主義的傳播,每一部分都圍繞著一個具體的城市展開,或者是兩個城市一起:巴黎,柏林,佛羅倫薩-羅馬,莫斯科,紐約。從檔案性的資料里進行挑選,這本書成為了一本重要的學術性作品,體現(xiàn)了近二十年來的調查研究。
MART展覽通過對具體客體的深思熟慮的并置,建立起一個共鳴的網(wǎng)絡,而沒有按照藝術史常規(guī)的單向路線進行,羅伯特?德勞內(Robert Delaunay), 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卡西米爾?馬列維奇(Kazimir Malevich)和其他人作品,在此發(fā)揮了不小的作用。通過將意大利藝術家和他們海外的先鋒派兄弟們聚合起來,展覽重新解讀了未來主義:它強調了一直潛在于意大利運動中的抽象性元素,這一元素在早些年里并不明顯。波丘尼(Boccioni)的大型油畫《人體的活力》(1913),塞維里尼的《光下的舞者的形狀》(1912),都值得一提。以萌芽狀態(tài)的抽象性來思考未來主義,而不是強調圖解的現(xiàn)代性,使得我們研究的課題變得疏離起來,從而給予它新的厚度和廣度。在運動本身精神的推動下,MART對于未來主義的觀點期待著下一場偉大的盛宴的開始—-即抽象主義的百年慶——是的,它很快就會到來。
作者瑪瑞亞?高 (Maria Gough)為哈佛大學現(xiàn)代藝術Joseph Pulitzer Jr教授。
— 文/ 瑪瑞亞?高 | Maria Gough, 譯/ 王丹華advertiser linksArario Galle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