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璽印,肇端于殷商,茂于東周,而成熟于兩漢。元明之際王冕、文彭已開“文人篆印”之風,吾丘衍《學古篇》印論的學術總結當是印章成熟的標志。清代金石學的興盛,更將印章的創作和學術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但是,真正“自覺”將璽印系統地放在“文化”的視野中來審視、考察與研究,大概要到20世紀20年代,以羅福頤的《古璽匯編》、《秦漢南北朝官印征存》等為代表。最近,徐暢先生的專著《先秦璽印圖說》(以下簡稱《圖說》)是一部融先秦璽印史、考證、文化闡釋以及古文字流變為一體的印學專著。
該著將先秦璽印進行分類、考證源流,從典章制度、經濟、哲學、軍事等幾十個方面進行文化性的闡述、縱橫剖析,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和開創性意義,具有以下四個特點:
一是系統性。中國傳統的文藝理論,往往表現出“非系統性”的特點,多為感悟、語錄式的承載方式。這顯然不利于文藝理論的獨立和現代學術體系的構建。特別是書畫理論,更多的是詩意性的評論和感悟式的審美體驗。印論多以印說、印話、論印詩詞等方式存在于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之中。顯然,這不但不能適應現代印學研究的要求,也難以描述璽印存在的歷史史實和印學研究向更深、更廣、系統的目標發展。這部《圖說》是一部系統性的研究先秦璽印的學術專著。他將先秦璽印分成濫觴篇、起始篇等30個獨立篇目,各篇目之間又互為聯系、照應,聯屬一體,不但運用和吸收了最新的出土資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將璽印的系統化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填補了先秦璽印研究的空白。
二是文化性。書法篆刻的“非系統性”,最大的缺陷就是沒有構成獨自的學術體系、縝密的思維結構和豐富的文化內涵。任何文藝種類缺少“思想性”一定是非主流的文藝,而不能對社會產生更多的影響和作用。傳統的印學,其發展歷史雖然已500多年,但其印論多止于“以印說印”、“借印說印”,難以宏達、深廣,這不但不符合歷史的事實存在,更難和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整體性”相一致,也不利于現代印學的學科建構。因此,璽印的“文化性”一定是印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當然,這種研究的高度和深度,也和現代學術的發展以及大量先秦史料、實物的新發現為前提。這部《圖說》最大的貢獻是將先秦璽印放在“文化”的視野中來觀察,與政治、經濟、哲學、軍事等十幾個領域相關聯,幾乎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這顯然是從傳統的印學研究向“文化性”研究的方面拓展,大大開拓了印學研究的廣闊空間。如“以印證史”,由于先秦歷史文獻的闕如,《圖說》依靠已有的先秦璽印文字,推演出當時的社會生產現狀和歷史事實,以達到“以印補史”的目的。
三是“正篆”性。我們知道,在現代篆刻和篆書創作中,存在“用篆和釋篆”等問題。小篆有《說文解字》查考,在篆字上還比較好處理,但是對于大篆的“用篆”就沒有這么方便。所以,創作大篆書法和先秦古璽印對當今書壇特別是年輕書家、篆刻家就比較麻煩,也出現過大量的訛錯。此事似小,其實很大。如果說當今書壇在傳統文化性上存在著嚴重不足的話,那么這種“用篆”舛誤、隨意、缺少深厚古文字知識積淀的狀況,就是這種缺失的具體體現。這部《圖說》專著在全面介紹璽印的起源和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各個領域知識的同時,更對先秦璽印的出土情況、存在方式、印文考釋、文字演變以及文化內涵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論證,從根本上解決了“印文”的用字問題,對“正篆”起到了非常大的現實作用。可以肯定,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部《圖說》將越發顯現出獨特的現實意義和文化、藝術價值。
四是“二重證據法”。如果說,以上“三性”是這部專著特有個性的話,那么,他的研究方法更具有現代性和科學性。他采用傳統研究方法與“二重證據法”相結合的新嘗試。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將璽印、封泥與古文獻相對勘是古璽印研究的重要途徑”、“璽印和文獻資料、漢畫像磚相印證,也是璽印斷代的重要方法。”王國維在上世紀初提出的“二重證據法”的研究方法,被現代學者充分肯定和廣泛運用。我們知道,中國史學傳統和西方史學有很大的不同,它更少神話色彩,因此,中國的史學從主體上來看是一部“信史”,因此,傳統學術研究多采用“以史證史”、“從文獻到文獻”的研究方法,導致“考古學”極不發達,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直到“殷商發掘”才開始。所以,由地下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是傳統方法論的突破。《圖說》很好地運用了這一方法,充分利用和發揮了近代以來的大量考古發現和最新學術成果,使其在印學研究方面更具方法論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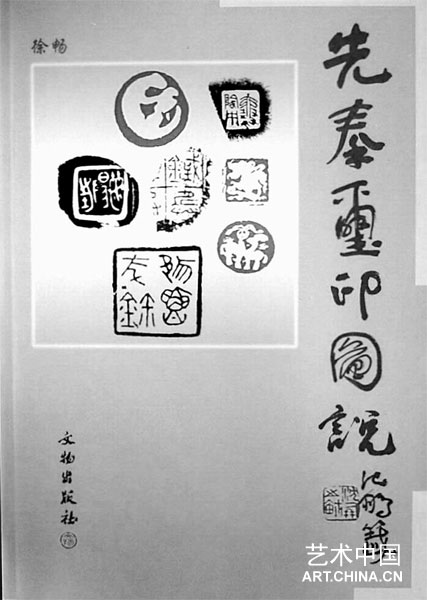
《先秦璽印圖說》封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