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浩立
從疫情開始到現在已有三個月余,身處藝術場域,提醒自己應該時刻處于一個反思與持續思考的狀態中,從之前寫的文章中談到了“集體歷史記憶”和“精神廢墟”,而第三篇我試圖從形而上的思想下沉到當下的藝術狀況,重啟一次生命時間,讓藝術成為一種可以持續思考的力量,提供一個方向,尋找一條可以讓生命平衡的路途。
在充斥著一切的飽滿情緒到來的時候,不論是抵抗、宣泄還是告誡、共情,這是情感面貌在經歷一種特殊狀況后的表達。但我們依舊需要回歸冷靜,在恰當的時刻留有一個空間讓自己反思。但有時候反思只是對情緒的暫時休眠,因此能夠培養一種持續思考的能力對于今天所發生一切的事實情狀來說尤為重要。

“疫情都市:既遠又近”,2019年,大館圖片來源:藝術新聞中文網
回溯到2018年,英國惠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就已經發布了一個跟傳染性疾病有關的藝術文化項目,這個藝術項目的創意總監肯·阿諾德(Ken Arnold)將之命名為“疫情都市”。這個舉動事實上早于今年發生新冠疫情之前,這個藝術項目旨在探討了“疾病如何影響人類健康,城市如何受其影響而演變的歷史”。當今天人們在消費社會和信息技術時代來臨的高峰時刻被突如其來的疫情所襲,所有的資本、股市和娛樂變得不堪一擊。

爆炸理論(Blast Theory),《A Cluster of 17 Cases》,2018年,圖片來源:藝術家組合爆炸理論(Blast Theory)
這一系列問題的發生以及如何解決,最終會被寄托時間,而時間作為一種歷史的雕刻者,不可能掩蓋和緩解傷痛。因此重啟時間,意味著將歷史記憶作為可以反思的深刻對照,同時讓其打開一個通道,進行自我救贖。
對生命政治的重新審視
對于生命政治這一概念的提出最有影響力的人應該是法國學者,米歇爾·福柯。他在生命政治概念的分析中談到了“現代生命政治”,它和古代生命政治恰恰相反,表面上看上去它是一種顛倒,其實并不是顛倒這么簡單,它暗敷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現代性中,形成了對生命的控制和管理,例如要讓人活得更好,更安全,更健康,更豐富,就是要讓生命成為統治的治理對象。由這一點出發,英國社會學家尼古拉斯·羅斯(Nikolas Rose)認為,“18、19世紀生命政治是一種健康政治,是關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政治,關于疾病和傳染病的政治,關于管制水、污物、食物、墓地的政治。”這兩位學者其實從生命政治發展的裂變過程中有耦合之處,基本上由對生命的控制發展到與生命息息相關的疾病、健康、醫療和食物問題上。
在前不久《藝術新聞Art News》刊登了魏穎的一篇文章《病毒、藝術與未來的生命政治》,其中她談到生命政治在經過時代的不斷沖刷之后,有了轉向。她寫到“未來生命政治是朝向技術創新和生物經濟學開放,并伴隨著生命倫理、生物安全性等更多的挑戰出現,藝術在這個時期也可以作為一劑良藥介入社會之中。”我對此產生共鳴,畢竟生命政治不應該只聚焦在政治的層面來談新自由主義問題,而應該將其回歸到現實語境中來審視當下發生的一切。特別是將生命政治介入到藝術創作和對社會現實的一個反思過程,這種表達在一定形態和方式上肯定能夠成為我們在生命倫理、生物安全和生命健康問題之外的一個可用路徑。
打開替代性藝術空間的大門
最近,藝術批評家姜俊提到了“替代性藝術空間(Alternative art Space)”這一概念,它是一種由藝術家和文化生產者自發管理和經營的空間。這樣一種自發性其實本就回到了和藝術主體相似的狀態中了,因為在藝術家和文化生產者的關系中始終存在一個商業利益的關系,但自發性的開啟它脫離了商業藝術畫廊的模式,營造出了一種新的藝術生態模式,能夠以這種方式激發藝術家進行自己的創作,特別是在疫情形勢下催生出了藝術環境的生態模式和存活樣態。
商業畫廊一直在所屬的商業圈層和既定的主流藝術欣賞價值的范圍里循環往復,當很多繪畫被資本關系及其階級所籠罩后,畫廊的呈現以及藝術品的收藏則會失去自我話語,形式的單一化、場地的商業化,藝術自身的主體性和生態環境也會逐漸失去活力與個性。比較著名的“替代性藝術空間”是由霍莉·所羅門夫婦在美國紐約蘇荷區經營的非商業展覽空間98 Greene Street,當時這個空間里除了藝術家作品的收藏展示之外,還有戲劇演出,詩歌沙龍活動以及藝術家進行實驗藝術的空間。

霍莉·所羅門畫廊(Holly Solomon Gallery)
替代性空間其實為今天受到疫情影響的所有藝術機構也打通了新的道路,特別是在遭到經濟重壓下面臨生存問題的時候,替代性空間無疑是一塊可以讓藝術家、文化生產者一同參與進行耕作的藝術試驗田。依托收藏和展覽進行銷售的同時,可以補給藝術家自由創作的實驗空間,帶動其他文化藝術形態和類型藝術在這個空間中一同生長,既打造了藝術空間作為社區的生產自治,也實現了藝術的多元和自由化發展。這種方式可能會縮減畫廊自身的營業成本,同時還會有更多藝術家和文化生產者的共同參與,在疫情過后的時期,這樣的藝術生態應該成為更多城市和地區營造替代性藝術空間缺位問題的借鑒范式。
藝術成為一種持續思考的力量,它會針對一切直指生命的問題,并以清醒的認知和方式來解釋。除了藝術以及自身的市場問題之外,還有關于藝術最終如何形成對生命的解答。如果說生命政治讓我們看到科技和醫學發展面臨的更多問題,并讓我們找到了藝術介入社會的方式,那么藝術則能成為我們重新審視的認知方式。同樣,面對今天整體的藝術環境,提出對“替代性空間”的建構意圖,是在試圖改良僵化的藝術市場和被商業資本關系暗敷下的藝術生態。
今天談生命政治不單單是從生命醫學、生命倫理在今后對人的肉身的關注,精神意識、思想引導以及生命的救贖則要回歸到精神層面上去。我們如何面對未來,如何承擔過去,這需要在當下重啟時間,在持續思考中不斷嘗試“縫合”。
(本文作者為青年藝術批評家、四川傳媒學院教師)







49a35649-7076-4dde-b5ea-6a6c985ca42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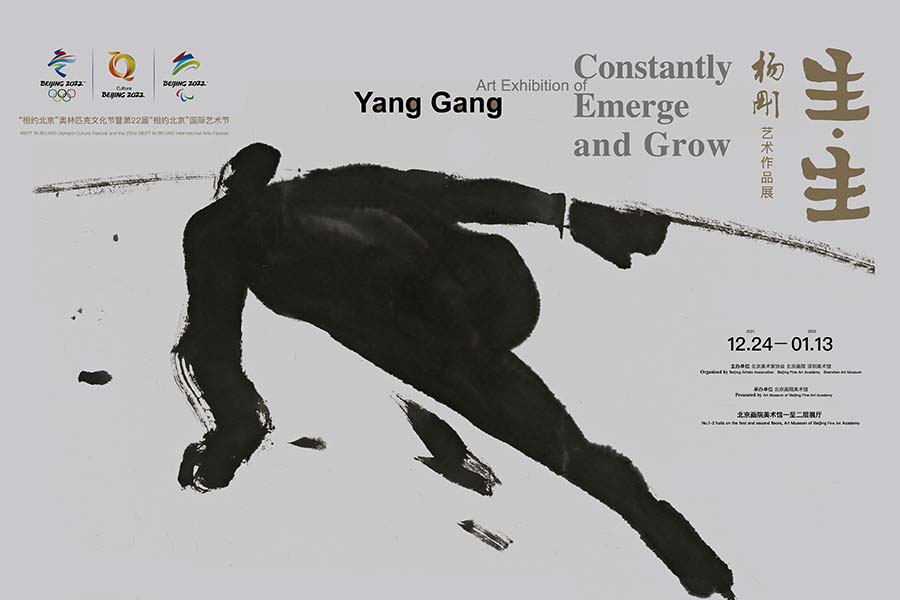


 主站蜘蛛池模板:
俄罗斯乱理伦片在线观看|
91一区二区在线观看精品|
亚洲乱码日产精品BD在线观看|
公交车被CAO得合不拢腿视频|
国产凌凌漆免费观看国语高清|
国产欧美综合一区二区三区|
国产精品东北一极毛片|
国产真实伦对白视频全集|
国产精品v欧美精品∨日韩|
国产对白精品刺激一区二区|
国产成人av一区二区三区在线观看|
国产三级理论片|
卡一卡二卡三专区免费看|
免费观看国产网址你懂的|
偷窥自拍10p|
亚洲熟妇色自偷自拍另类|
亚洲aⅴ在线无码播放毛片一线天|
久久久综合香蕉尹人综合网|
久久久久免费精品国产|
中文无码AV一区二区三区|
两个人看的www视频免费完整版|
一级国产黄色片|
a级在线免费观看|
99久久婷婷国产综合亚洲|
91麻豆高清国产在线播放
|
亚洲香蕉在线观看|
亚洲欧洲日产国码av系列天堂|
亚洲伊人久久大香线蕉综合图片|
久久精品视频一区二区三区|
久久久久久国产精品mv|
一区二区三区欧美日韩国产|
99ri在线精品视频|
青柠直播视频在线观看网|
紫黑粗硬狂喷浓精|
欧美在线视频免费看|
波多野结衣和黑人|
日韩乱码人妻无码中文字幕
|
欧美性色黄在线视频|
日韩欧美国产综合|
性护士movievideobest|
国产精品亚洲专区一区|
主站蜘蛛池模板:
俄罗斯乱理伦片在线观看|
91一区二区在线观看精品|
亚洲乱码日产精品BD在线观看|
公交车被CAO得合不拢腿视频|
国产凌凌漆免费观看国语高清|
国产欧美综合一区二区三区|
国产精品东北一极毛片|
国产真实伦对白视频全集|
国产精品v欧美精品∨日韩|
国产对白精品刺激一区二区|
国产成人av一区二区三区在线观看|
国产三级理论片|
卡一卡二卡三专区免费看|
免费观看国产网址你懂的|
偷窥自拍10p|
亚洲熟妇色自偷自拍另类|
亚洲aⅴ在线无码播放毛片一线天|
久久久综合香蕉尹人综合网|
久久久久免费精品国产|
中文无码AV一区二区三区|
两个人看的www视频免费完整版|
一级国产黄色片|
a级在线免费观看|
99久久婷婷国产综合亚洲|
91麻豆高清国产在线播放
|
亚洲香蕉在线观看|
亚洲欧洲日产国码av系列天堂|
亚洲伊人久久大香线蕉综合图片|
久久精品视频一区二区三区|
久久久久久国产精品mv|
一区二区三区欧美日韩国产|
99ri在线精品视频|
青柠直播视频在线观看网|
紫黑粗硬狂喷浓精|
欧美在线视频免费看|
波多野结衣和黑人|
日韩乱码人妻无码中文字幕
|
欧美性色黄在线视频|
日韩欧美国产综合|
性护士movievideobest|
国产精品亚洲专区一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