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煉:你最早讀到的美術(shù)理論譯著是哪一部,對你有什么樣的影響?
段君:貢布里希的《藝術(shù)發(fā)展史》(天津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可能很多藝術(shù)界的同仁都有相同的經(jīng)歷。雖然它并不是嚴(yán)格的理論譯著。盡管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覺得《藝術(shù)發(fā)展史》在材料上不夠詳盡,部分細節(jié)的討論展開得并不充分,在研究方法上也中規(guī)中距,但我當(dāng)時閱讀它的感覺是:西方藝術(shù)竟然如此富有思想性。范景中先生的翻譯亦令人神往。相比之下,國內(nèi)有關(guān)中國美術(shù)史的著作對中國藝術(shù)品在思想和哲學(xué)層面的討論一直較為貧瘠,后來洪再新等學(xué)者因吸納西方藝術(shù)史家對中國藝術(shù)史的研究,才使得國內(nèi)對中國美術(shù)史的敘述具有思想的自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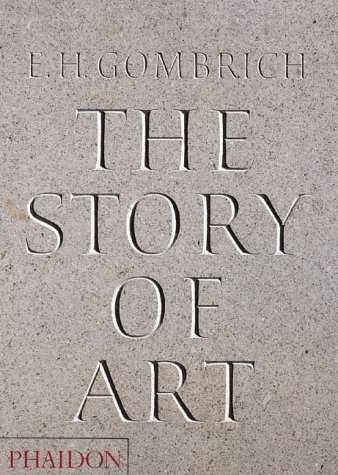
段煉:你是否從事過美術(shù)理論的翻譯,主要翻譯了哪些作品?
段君:2009年5—6月翻譯過關(guān)于貧窮藝術(shù)的文章《調(diào)查:動物、植物與礦物現(xiàn)身藝術(shù)世界》,四萬余漢字,原著是意大利著名策展人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她已被選為2012年第13屆卡塞爾文獻展的藝術(shù)總監(jiān)。但對該文的翻譯完全超出我的能力范圍,頗費思量,畢竟我從事翻譯的經(jīng)歷不足掛齒,僅在求學(xué)期間選修清華大學(xué)歷史系劉北成先生的《西方思想史概貌》課程時有過嘗試。劉北成先生翻譯過很多福柯的著作,比如《規(guī)訓(xùn)與懲罰》、《瘋癲與文明》、《臨床醫(yī)學(xué)的誕生》,他布置的課程作業(yè)是翻譯有關(guān)啟蒙運動的文章,當(dāng)時我初次涉足翻譯,但結(jié)果是讓我對翻譯產(chǎn)生嚴(yán)重的挫敗感。
段煉:在翻譯過程中遇到特別的概念而又沒有現(xiàn)成的中文對應(yīng)術(shù)語時,你怎么辦?是自創(chuàng)一個(例如“有意味的形式”),還是借用一個?
段君:自創(chuàng)。勉強借用中文術(shù)語,可能會誤入歧途,畢竟已有的中文術(shù)語在歷史中已經(jīng)積累豐厚的內(nèi)涵和語境,而且自創(chuàng)術(shù)語必定會豐富漢語寫作——當(dāng)然自創(chuàng)的術(shù)語要適當(dāng),盡可能避免生僻的字眼和僵硬的組合。自創(chuàng)術(shù)語并不僅僅意味著漢語詞匯的增加,更在于從寫作的文法結(jié)構(gòu)和思維習(xí)慣等方面沖擊原有的漢語。魯迅早在1931年的《關(guān)于翻譯的通信》文中說:“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去熟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借助于粉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要醫(yī)這病,我以為只好陸續(xù)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后來便可以據(jù)為己有。”[i]在嚴(yán)復(fù)翻譯的時代,更多的是用文言文翻譯西學(xué),現(xiàn)在看來顯得不倫不類,對漢語寫作本身沒有發(fā)生效力。
段煉:在技術(shù)的層面上,你對最近三十年來美術(shù)理論的翻譯狀況有什么意見?例如外行譯者翻譯美術(shù)理論造成誤導(dǎo)。
段君:技術(shù)或?qū)I(yè)技能是美術(shù)理論翻譯的基礎(chǔ),它直接導(dǎo)致翻譯的準(zhǔn)確性。我曾讀過《20世紀(jì)藝術(shù)的語言觀念史》,由時任浙江經(jīng)濟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副教授的劉一平女士組織該院外語教師翻譯,里面有大量的錯誤。我個人不太傾慕外行的翻譯,外行通常不了解西方前沿學(xué)術(shù)的進展,所以很多術(shù)語都沒有翻譯成通行用詞。但藝術(shù)內(nèi)行的翻譯所存在的問題也顯而易見,不少內(nèi)行原非外文專業(yè)出身,在語言理解的準(zhǔn)確性方面沒有保證。技術(shù)層面最常見的問題是翻譯的順暢與否,如果自己沒有讀懂,翻譯出來的語句肯定令讀者苦不堪言。
魯迅寧愿“信而不順”,而不肯“順而不信”,他提醒讀者,表面上讀來通順無比的譯本反而更需警惕:“譯得‘信而不順’的至多不過看不懂,想一想也許能懂,譯得‘順而不信’的卻令人迷誤,怎樣想也不會懂,如果好像已經(jīng)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今天的讀者已經(jīng)很難有耐心在看不懂或文法不通的語句面前再“想一想”。與此相關(guān)的是譯者自身的語言造詣,我的切身體會是,同一位西方作者會因不同翻譯者的行文,其著述會產(chǎn)生很大的區(qū)別,比如德勒茲,早期我看過一本《時間-影像》,因為譯文干澀,對我沒有產(chǎn)生太大的吸引力。后來再看《哲學(xué)與權(quán)力的談判:德勒茲訪談錄》,竟然迷戀上德勒茲,其中很大的原因是這本書的翻譯語言雋永。
段煉:在學(xué)術(shù)的層面上,你對最近三十年來美術(shù)理論的翻譯狀況有什么意見?例如,在21世紀(jì)的當(dāng)代藝術(shù)語境中,還有無必要譯介形式主義,為什么?
段君:近三十年來美術(shù)理論的翻譯工作值得歷史記載,但總體狀況差強人意,雖然最近在易英、常寧生、沈語冰、王春辰等學(xué)者的勤苦工作下,局面已經(jīng)發(fā)生很大程度的改觀。我沒有資格對翻譯現(xiàn)狀進行指責(zé),而且我也是出于對美術(shù)理論翻譯事業(yè)的尊重和期待。我從事藝術(shù)批評工作的思想資源近半是翻譯成中文的西方思想或哲學(xué)著作,美術(shù)理論譯著的啟發(fā)為數(shù)不多。最近三十年西方藝術(shù)理論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等方面都已發(fā)生巨大的變革,西方藝術(shù)批評界的學(xué)者以及人文社科界的思想家采用前沿方法來研究中西方傳統(tǒng)藝術(shù)或全球當(dāng)代藝術(shù)的著作批量問世,但因為中國藝術(shù)界的翻譯工作沒有及時和系統(tǒng)地跟進,所以無法為如何運用前沿藝術(shù)理論研究中國傳統(tǒng)藝術(shù)和當(dāng)代藝術(shù)的具體實踐提供優(yōu)良的范例,中國的藝術(shù)批評家只能自我摸索,沒有把握住參照和借鑒的機遇。
至于形式主義的譯介,肯定是有必要的,舉例來談,我讀過汪民安先生的文集《形象工廠》,里面收錄的是他對中國當(dāng)代繪畫的分析文章,寫作模式相對固定,即根據(jù)畫面中的某類形象或某種場景進行意義追加,比如鳥獸、煙霧、排泄、嘔吐、電視機等等,行文本身是令人信服的,但熟悉西方現(xiàn)當(dāng)代學(xué)術(shù)思潮的讀者會很容易看出汪民安的闡釋工具是福柯、德勒茲、尼采、海德格爾等人的哲學(xué)和思想,其中欠缺的正是對形式主義批評理論的研究和使用,最終導(dǎo)致的負(fù)面結(jié)果是,《形象工廠》中討論的所有畫作如一人所為。沈語冰先生曾引述批評家列奧·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1920-2011)對形式主義理論的批評性總結(jié):在形式主義倫理中,理想的批評家不為藝術(shù)家的表現(xiàn)性意圖所動,也不受其文化的影響,對其反諷意味或圖像學(xué)內(nèi)容視而不見,目不斜視地按計劃行事,就像奧爾弗斯(Orpheus)走出地獄一樣。簡而言之,形式主義批評更注重線條、顏料、節(jié)奏、結(jié)構(gòu),尤其關(guān)心各形式元素之間的關(guān)系。而對符號進行意義的追加可能會讓讀者與藝術(shù)的真實漸行漸遠,繼續(xù)譯介形式主義理論也是為修復(fù)或增強批評家對藝術(shù)的敏感。
段煉:在藝術(shù)院校的史論教學(xué)中,你認(rèn)為學(xué)習(xí)美術(shù)理論譯著有多重要?例如:你在教學(xué)中常用翻譯的理論、概念、術(shù)語嗎?
段君:除了研習(xí)西方美術(shù)理論的觀點和研究方法,我認(rèn)為更重要的是在學(xué)術(shù)上培養(yǎng)開放的心態(tài)和寬闊的視野。我時常使用翻譯成中文的理論和術(shù)語,因為相當(dāng)多的命題必須是用專業(yè)的術(shù)語才能表述得更準(zhǔn)確,其實部分學(xué)生也希望研習(xí)更多的專業(yè)術(shù)語。如果為迎合聽眾,刻意避免術(shù)語并改用通俗的詞匯,學(xué)生反而會覺得課程沒有挑戰(zhàn)性或新鮮感。但由于目前部分學(xué)者在寫作或講演中對術(shù)語的使用仍屬囫圇吞棗,現(xiàn)在依然很難估量術(shù)語的作用。
段煉:你怎樣將西方美術(shù)理論用于你對中國當(dāng)代美術(shù)的研究?
段君:中國當(dāng)代藝術(shù)置身于全球藝術(shù)體系,以更具全球性的西方藝術(shù)理論來研究中國當(dāng)代藝術(shù)并非不合適,只不過要實時考慮到中國藝術(shù)的歷史因素,不能忽視中國藝術(shù)的歷史和理論對中國當(dāng)代藝術(shù)(批評)可能產(chǎn)生的影響。客觀地說,中國傳統(tǒng)藝術(shù)理論很難以當(dāng)代藝術(shù)為對象,排斥反應(yīng)的癥狀非常明顯,因為囿于歷史局限,傳統(tǒng)理論并沒有把全球因素考慮在內(nèi),而且西方理論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思想展開得特別充分并且系統(tǒng)化,但中國傳統(tǒng)理論的主流講究點到為止,以致語焉不詳,如果不經(jīng)過調(diào)整,依舊難以適應(yīng)現(xiàn)當(dāng)代學(xué)術(shù)的推進與發(f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