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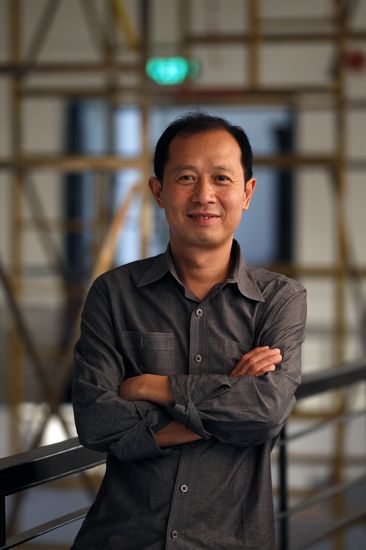
獨立策展人侯瀚如 許海峰 圖
國際上頗具影響力的知名華裔策展人侯瀚如有十余年的國際策展經歷,從1994年芬蘭的“走出中心”,1997年的“運動中的城市”,南非“約翰內斯堡雙年展”,威尼斯雙年展,上海雙年展,這十余年中的絕大部分時間,侯瀚如是沒有一個“單位”支付給他固定工資的,侯瀚如說自己是一個自由的、獨立的策展人。
藝術評論:如何能讓藝術家在策展人所界定的主題當中獲得更多的自由,或者是藝術家的作品拓展了你的主題?
侯瀚如:對,當然我覺得藝術家的自由是首先要考慮的,我從來都覺得一個展覽如果把藝術家的作品作為一個主題的插圖,那是最糟糕的,而實際上你提出的這個所謂概念或者我一般都叫conceptaul
framework概念架構,這個東西只是給予藝術家的創作一個定位,但是他本身的概念是相對來說比較獨立的東西,我只是把這個相對比較獨立的東西放到一個更加廣泛的定位里面,然后在這個里面他可以成為一種公共話語,因為和這個定位發生關系同時也令觀眾可以參與進來,這樣的話會形成閱讀上的開放性,或者是后現代主義提到的“作者之死”,這種說法、關系我覺得藝術作品的意義并不是很簡單的、封閉的、固定的,它仍然是在不斷地被闡釋當中,所以我們做展覽的本身就是把闡釋的過程加以更加有意思的強化。
藝術評論:策展人其實也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幾年前連策展人的概念都沒有,在1997年的時候做策展人和現在做策展人感覺上有什么不一樣?
侯瀚如:從根本上來說我學會了越來越多種的跟更加具體的環境打交道的一些方式,而十幾年前,我更強調是自我組織的、即興的、臨時的策略,來把一些作品的獨特方面和能量表達出來。但是今天可能有一個很大的改變,就是當代藝術變成了越來越官方化,我的意思不是說變成官方的東西,而是正式化、體制化,就是說做藝術有了套路了。然后接下來還有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就是市場的影響越來越大,藝術變成了一個正正經經的市場上的一個產品,這個時候我們怎么去面對這種市場化、體制化的背景,還能夠使得藝術它本身超越這樣一種限制,而保持它在精神上面、智力上的獨立性和完整性?
這就是說現實比十幾年前更加具有挑戰性,策劃人面對的精神上的要求更高。十幾年前實際上更自由,
藝術家的創作方式也非常不一樣。現在藝術家的素養,比十幾年前高很多很多,展覽多了很多,博物館多了很多,
雜志什么的也多了很多,各方面都多了很多。
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一個問題,第一就是作品的質量普遍在提高,但同時它越來越失去尖銳性,越來越失去這種個別、金雞獨立的、突出的性格。這是一個矛盾。
藝術評論:這是一個國際化的問題嗎?
侯瀚如:當然是。中國基本上就是更加有效率,但是更加臨時的,質量更低的國際化傾向的一個版本,就好像中國的生活非常昂貴,但是都是一種非常廉價的、沒有質量的昂貴。這對于我們策展人來說也是挑戰,策展人本身,在十幾年以前并不是一個主導,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行當,有學可上,有書可看,這樣的話變成了條條框框很多,而且我們現在都在教學生怎么去做一些好的展覽,好像好的展覽是可以很明確地去描述的。但實際上,就我個人來說,我一直覺得越是這樣明確的話就越是要想辦法把它打破。
藝術評論:以中國目前的情況來說,你覺得什么樣的展覽才是一個好展覽?
侯瀚如:如果以中國目前的情況來說,能做得好的展覽就是,很認真、很準確地把作品的完整性表達出來的一個展覽,把作品的真正的內容和學術的藝術純粹性,它的力度表達出來,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其實誰也不能說畫抽象畫就比做錄像的低級,但是實際上都不是那么簡單的。但你做一個展覽的話,就算你做一個古董的展覽,你還得把古董里面所含有的歷史背景、作品在歷史背景里的獨特性能夠用一種很敏銳的方式,把它表達出來,然后把作品像一個活著的生命一樣,呈現在別人面前。作品不是一個死的東西,它必須是活的,這個不光是針對中國了,對全世界都是這樣。我們的問題就是,我們經常教學生怎么去做好的展覽,這是把展覽作為一個死的東西去看,而沒有辦法使別人感受到這些東西是活的,它背后的藝術家,它背后的生命。有一天這個作品因為物質的原因,可能會死掉,會消失掉。做展覽就是要把這些東西的生命在一個空間里面表達出來,就是要把作品活生生地展現出來。
為什么我們需要展覽?為什么藝術家的東西可以上網 隨便就能看到很多東西?為什么我還要去看展覽?因為它是全身心的一種感受。
藝術評論:策展人還身兼批評家的角色。
侯瀚如:策展人不是身兼,他就是批評家。如果策展人不是批評家、不是一個藝術史家的話,他就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個工作人員,他跟那個美術館里面看門的沒有任何區別。
藝術評論:策展人身兼了一個發掘人、批評家的角色,甚至有些策展人還會在當中參與一些畫廊、畫作的經營,參與買賣。
侯瀚如:這個和我沒什么關系,這個是別人要干的事情。當然不可能每個人做事都非常單純,我也要做其他很多各種各樣事務性的事情,我也要去找錢、做很多社會關系的事情,比如說我現在也在管兩個部門,我的學校里面的兩個部門,那么就有很多日常的、行政的東西,每做一個展覽都有很多行政性的事務非常多,那么這個東西你不可能純粹是一種文化上的,藝術上的東西,雖然我們花很多開支,70%~80%以上的時間去做很多很零碎的事情、辦公的工作,但是我覺得我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原則,就是我的工作,我自己的工作絕對不會是一種盈利的目的,當然不可避免地誰都要掙錢、吃飯交房租的。
藝術評論:確實不太看到過你有商業文章。
侯瀚如:這是我的原則,從來不做。我可以給藝術家的畫冊寫文章,因為他們是我喜歡的藝術家。但寫這個文章有很微妙的一點——因為你給一個畫冊寫文章,往往都只能夠寫一些比較正面的東西,但是我為什么接受寫這個東西?是我覺得這個藝術家的作品是好的,他是一個好的藝術家我才會去寫。我不會隨便接受一個任務,因為人家給我很多錢我就去寫一篇應景的文章,所以說這個東西就和廣告完全不一樣,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寫文章的時候很像寫廣告,那是個人的選擇問題了。
藝術評論:你策劃過很多國際展覽,比如伊斯坦布爾,也做過廣州雙年展和2000年的上海雙年展,你覺得國際策展和國內策展的經歷有什么不一樣嗎?
侯瀚如:國內也有一些相當不錯的策展人,當然從總的角度來說我覺得,像我們大家都面臨同樣的挑戰,十幾年來藝術都變成了一個主流的一種,社會主流的一種高尚活動,有的時候甚至成了一種高級娛樂,這個時候其實就從職業倫理的角度提出了挑戰。
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解決的問題。當然你不可能離開現行制度,因為它就像空氣一樣的圍繞著你。要么你就徹底不要做展覽,但是如果你繼續要做的話,必須要跟各種各樣的市場、機構打交道,那么這個時候我們有一個責任,要不斷地提醒自己還有和自己合作的藝術家和機構,我們干這個事情是為什么。
可能在美國的策展人更有一種知識分子對待藝術的態度。但是他們中的多數要不就是學院派,要不就是在非營利機構工作,比較順從、規規矩矩做事情。我覺得中國好像這兩方面都沒有。就是說學院派也好、很規矩的策展人、知識分子的策展人都沒有,這些成分都很少,而更多的是為了應付、回答一個馬上就要實現的任務,很事務性。
國內的策展人很少有一個對藝術的個人信念,就是說“我相信藝術應該就是這個樣子”。我覺得有這樣信念搞藝術才是對的。國內的一些策展人可以把一些商業畫家和嚴肅藝術家如黃永砯等放在一起,這對我來說是難以想象的。對我來說黃永砯是藝術家,那些商業畫家就不是藝術家。
在國內做一個藝術家好像很容易,但不少人沒有自己的藝術信念,沒有自己的藝術價值的標準,那么他們可能會做很多作品,但是這個很多東西對我來說不是藝術。
藝術評論:那你的藝術信念是什么?
侯瀚如:這個對我來說可能更多的是它用一種非常個人的、獨特的語言,但是同時又能說出一些對于我們的生活、內心生存狀態的一種有批判性的閱讀,這個對我來說是藝術的作用。然后從本體上來說可能它是給我們帶來看世界的另外一種方式并付諸實踐。你的做人的方式可能會很不一樣,所以這個也涉及到,就是說每個人的獨立的、知性的一種歷程,這是一個像生命一樣的東西,必須要有一種很特殊的生命形式,這個對我來說才叫藝術。
藝術評論:在國際策展上,你不把意識形態作為前提而跟當地的語境發生關系,那么國內的策展是不是會有更多的妥協?
侯瀚如:應該沒有吧,我想我不能做的我就不做。原因是,第一,可能邀請我做這個事情的人,他的目的和我的目的很不一樣,不一樣到沒有辦法達成共識,當然每個人要組織一個什么事情的時候他的目的可能和你的都不太一樣,但是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互相達成一種共識、可以合作的可能性;第二個,他對這個事情的期待和我對這個事情的期待是不同的,這個所涉及的道理還是要回到剛才關于藝術的信念的問題上去說,他想要的東西和我相信的東西是完全兩碼事,那么你再多的錢、再多的空間、再好的條件給我,對我來說我都不感興趣,因為我知道這個事情是做不好的,我不可能在一個做不好的事情上面簽字。就是說如果是我不想做的,我卻做了,回家會睡不著覺。
藝術評論:你那么多的策展經歷中有什么不可改變的基本原則或者說堅定的立場?
侯瀚如:我想有兩個原則,第一,我的這種精神上的和立場上的自由不能失去,第二個,真正的藝術家,他的自由不能因為參與了什么展覽而失去,這是我要盡我所有能力去保護的事情。如果這個事情做不到,比如說藝術家作品開幕之前還沒有裝好,那我絕對不能接受這個展覽開幕。
藝術評論:那么如果說展覽現場裝好以后,有當地政府或者有關機構要求這幅作品撤下來,你會照辦嗎?
侯瀚如:這個時候是非常困難的選擇,那么第一你首先要想到,在這個地方能做什么事情,因為有些事情是很無謂的一種挑釁。它可能會變得很廉價,那么這個事情就算做出來也沒什么意思。往往就是所謂被檢查掉的東西,很多這樣的東西,是很廉價的一種對抗,這個是沒有意思的,包括有些人,不想點名嘛,弄不好變成國際明星這種,很沒勁。這個對我來說和藝術沒有什么關系。還是回到我們剛才說的這個問題,就是,我們作為一個批評家,我們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作品,所以你才會去做這個展覽,做這個很自然的、很廉價的挑釁可能不太會存在于你的展覽里面,但是如果真是出現了這種情況,這個選擇要不就是機構讓步,要不我就辭職,我就不開這個展覽了。
藝術評論:但是也不跟他們妥協?
侯瀚如:那是肯定的。
藝術評論:你的策展經歷中有過這樣的事情嗎?
侯瀚如:幾乎沒有,因為可能我每做一個事情時,我都在想它在某一個領域、語境里面的合適性,而且就是說它長遠所帶來的,比如說2000年我做上海雙年展的時候,當然我也很想一步就達到所有的目的,給所有的藝術家自由,但是那個時候是不太可能,所以你必須要做一些很站得住腳的、示范性的東西,然后把這個形式慢慢形成以后。那今天,十年過去了,藝術家勢必會獲得更大的自由,我想這是肯定是的。那么今天就是另外一個課題了,我今天的課題就是“廉價的挑釁”。面對現實,你要有一個想好的底線,然后才去做,做的話,你不要期望一下子就可以達到目的,但是你要看到你做的事情的意義可能會影響到后面十年、八年的變化,所以你要做一個鋪墊的工作。
藝術評論:所以展覽實現的意義大過一切?
侯瀚如:展覽的實現有意義,但是絕對不能夠失去它的批判精神,展覽的批判精神可能并不是很簡單就像喊口號式的。
你仔細想一想2000年上海雙年展里面有一些政治上非常不容易被官方接受的東西,但是當時它可以這樣過去,這個展覽可以很順利地完成,大家都很高興,為什么呢?因為這些作品本身。它的這種力量并不就是僅僅回答你當時當地的一個幾乎很gossip一樣的話題的,像很低級的政治對抗的話題,而是更多的是從事情整體的命運,它的歷史,來發掘到它的政治的含義。這個東西它很強烈,同時它又不需要用很多碰撞來表達它自己。比如說黃永砯的作品《銀行的沙/沙的銀行》,把外灘的匯豐銀行的那個樓用沙子按比例復制了一遍。這個實際上是非常強烈的一個批判性的作品,對于上海的歷史、中國的歷史。但是它同時又涉及到不光是中國和上海,而且是全世界的這個從殖民主義過來的經濟體系,到今天我們對于現代化的追求的某一種荒謬的地方,實際上它都含在里面了,所以它這種批判性這是一種很廣義上的批判性,是最有力量的。對于我來說,感興趣的是這樣的一種作品,絕對不可能對那種很傻的、口號式的把兩個毛澤東的頭像放上去的,這種我不感興趣,這對我來說這根本就不是藝術。
藝術評論:你是覺得符號太簡單化?
侯瀚如:這方面做得好的話,實際上是不會引起太多的被檢查的可能性,如果這樣還被檢查的話,我很佩服這個檢查官,他的水平太好了。我也相信言論自由、表達自由。但它不是一個東西,它是一個不斷在不同的語境里面變化的過程,所以你怎么把握這個過程,你沒有絕對的自由,你不能夠說因為我是藝術家所以我就有絕對的自由,你也是個人,你也在這個地方,有些事情是有界限的,比如我們絕對不能夠支持種族主義、支持法西斯和各種強權。
藝術評論:西方其實也是有界限的。
侯瀚如:當然有界限,就是說,這個東西這是一個涉及到人的一個最基本的價值概念、價值觀念的問題,這個有體現,所以你不能為挑釁而挑釁。確實你也要從很多面的、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你在伊拉克,或者在沙特阿拉伯,你說伊斯蘭那里不好,就是有問題的。為什么?因為伊斯蘭它首先不是一個東西,而是一個廣為社會認同的信仰體系。而且你必須要尊重當地的歷史、風土人情,你必須用理性來面對它。
比如說宗教自由,宗教自由其實本身也是一種信仰,你看宗教自由這個在歷史的過程中是怎么過來的,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種針對某一種宗教的另外一種信仰,所以現代歷史的過程本身也包含了很多、很聰明的方式去處理各種關系,
包括自我和他人的關系的問題。
藝術評論:他們也許只是迷戀這種捍衛的感覺。
侯瀚如:很多激進動物保護主義者,宗教極端主義者去時不時會抗議一些藝術作品,但一般來說他們根本就沒有看過這些藝術作品,他們只是道聽途說,聽到別人說這個戲劇里面好像有反對基督的,他們就去,那前一陣子在巴黎就是這樣,后面有很多政治的操作,但是你去采訪這些人,你會發現他們對到底作品在講什么一無所知,他只是聽說它侮辱了基督教,一般來說就是這樣。
藝術評論:就好像對帕慕克的反對一樣,很多人都沒有看過帕慕克的書。
侯瀚如:所以我們的判斷必須依靠理性。用理性的方式弄清楚你為什么反對,我為什么反對,我為什么支持,那么這個時候對話是可能的,但是一般來說他們就會拒絕對話,因為忽然間他們發現他們自己是非理性的。
藝術評論:在2000年做上海雙年展的時候,你當時感慨萬千,這是什么樣的一種契機?
侯瀚如:當時確實我想的很多的一點,是剛才我提到的,在當時做上海雙年展是很特殊的,在2000年的時候,我是想后面十年對于中國的發展,能夠提供怎樣的一種前景,我們做的事情好像鋪路的第一塊基石,這種感覺還是很強烈的,當然這種強烈也來源于我們都知道在這之前多么不容易,確實那個時候我們經歷過80年代、90年代的,這種不容易當然就是說……
藝術評論:這種不容易是來自什么地方?
侯瀚如:其實當時當代藝術基本上都是地下活動,基本上都要躲起來做的事情。那個時候做藝術家確實是需要極其堅強的內心,而且我覺得當時的藝術家都是處于一種非常不正常的情況,因為它們在一種很特殊的環境里面,他們是在沒有物質條件的情況下做作品,他們有很好的想法,但是很難實現,而且如果能實現的話都是匆匆忙忙為了什么事情突然間像打游擊一樣的完成,那樣他永遠都做不出來一些很重要的作品,因為他沒有辦法有完整的條件和時間,這個是當時上世紀90年代初一直到2000年以前,中國絕大部分的當代藝術家都是為當時剛剛出現的國際市場去做作品,當時國內根本就沒有任何條件去靠藝術生存,而且甚至連展出都很困難。
藝術評論:是不是1992年到1993年最困難?
侯瀚如:對,那個時候也很困難,一直到2000年之前,實際上相對來說都不容易。同時來說藝術家、策展人都相當的臨時性,他們能做成一個展覽就走。那個時候基本上就是,誰說我昨天找到了一點錢,今天想一想,明天展覽就開幕了,都是這樣的。
藝術評論:當時的作品是怎么來的?
侯瀚如:作品就臨時趕啊,我可能是夸張了一點,可能只有一個星期去組織整個展覽,所有的作品都顯得非常的臨時性、沒有質量,它只能有點靈機一動的,絕對做不出來一種很完整的東西。
我當時有一種考慮就是上海雙年展能夠開成的話,其中的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能夠為創作條件的正常化提供一種開端,所以籌備的過程很關注于如何去讓藝術機構和文化官僚接受當代藝術,更重要的是還要獲得觀眾和媒體的支持。這樣藝術家的創作條件會正常些,
可能做出有深度的作品來。要達到目的就要費很大的勁,所有的感受加在一起就讓人很激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