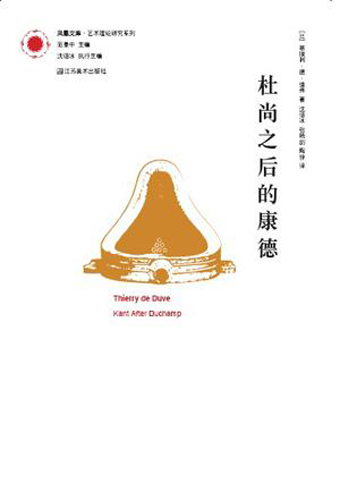
在這篇譯后記里,我不打算像以往那樣,從作者的生平寫起,然后是對作者思想背景的介紹,及其主要論述的梳解與評論;而是寫一下我對德·迪弗及其論旨的啟發性的一點思考。這主要是因為,作者的生平極其簡單,幾乎等同于其著作本身;而他在這本書里的論述也曉暢明了,大約已無需他人再作鄭箋了。
我想說的第一個啟示是,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并不像國人想象的那樣,有著一清二楚的界線:例如從時間角度說,20世紀60年代之前的藝術是現代藝術,之后的藝術是當代藝術;或者從哲學、理論或批評的角度說,以主體性為中心的、追求自律的藝術是現代藝術,而主張解構主體性、強調藝術的社會批判性的藝術是當代藝術;或者,從語言學的轉向角度說,以結構主義語言學為話語模型的藝術是現代藝術,而以后結構主義、語用學為理論范式的藝術是當代藝術——本人可能是國內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人。
如果我們稍微仔細地讀一讀德·迪弗的這本書,就會發現,以上種種區分是多么不可靠,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的界線又是多么含混而微妙。以本書的核心論題即杜尚的現成品為例。試問杜尚的《泉》究竟是現代藝術,還是當代藝術?如果你認為它是現代藝術(這從歷史-時間上來說非常合理,因此許多歷史學家把杜尚刻畫為一個達達主義者、一個歷史上的先鋒派),那么,這就與以現成品(物性),或觀念(理論)為主導的當代藝術的習見相沖突。如果你認為它是當代藝術(這從理論-觀念的角度說也非常恰當,因此許多理論家將杜尚當作觀念藝術/當代藝術的始祖,從而成為“藝術終結”,或者哲學對藝術的褫奪的典范;從杜尚到沃霍爾和博伊斯,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一條線索來),那么,這卻與杜尚早期隸屬于立體派運動,稍后又成為達達主義運動的重要一員(盡管德·迪弗對此頗有異議)的歷史事實不相符。
德·迪弗此書的重大貢獻之一,便是還原了杜尚小便器出籠時的那個藝術史現實(參見本書第二章)。他著重梳理了杜尚的立體派作品《下樓梯的裸體》在巴黎秋季沙龍被拒,卻在美國軍械庫畫展上引起轟動的史實。正是這些事實使杜尚意識到,“是觀眾創作了繪畫”,而且觀念比作品本身更重要;因為大量從來沒有看過《下樓梯的裸體》的美國公眾也都通過各種媒體“知道”這幅畫,而且“知道”杜尚就是那個制造了這一丑聞的法國藝術家。也許正是這些事實,使杜尚找到了心理平衡:如果說他在由其兄長出任評委的巴黎秋季沙龍上被拒的經歷令他隱忍的話,那么,軍械庫展覽后名聲如日中天的杜尚想到的就是,如何以新的幽默和機智抹去那段不光彩的歷史。所以,當紐約獨立藝術家協會力邀杜尚擔任獨立藝術家大展的組委會主席之時,這位能夠賦予美國紐約前衛派以法國巴黎前衛派光環的先鋒派的父系代表,便發現了殘忍而又冷酷的報復機會。眾所周知,這便是杜尚的小便器出場的語境。
杜尚的小便器令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膠著在一起,無法輕易加以區分。德·迪弗的抱負之一便是要解釋這一事實。他的解釋是否讓人信服尚可爭議,但他為此展開的理論探索所呈現出來的令人神往的一面,則早已有口皆碑。那就是德·迪弗的藝術唯名論。這個理論以杜尚的《泉》為鏈環,將西方自18世紀以來的藝術現代性歷史焊接為一個整體:西方直到此書出版為止時的現代藝術史,是一部將“藝術”理解為一個專名,而不是普通名詞或概念的歷史;此書出版后西方的藝術是否已經走出了這段歷史,則另當別論(作者明示“現代藝術”已經離開了現代性的星球,正因為這個他才有可能對它進行考古學研究;但這一點也正是可爭議之處)。在德·迪弗看來,杜尚的小便器如果離開了18世紀以來的法國藝術體制(先是沙龍展,接著是落選者沙龍,再接著是獨立沙龍),是完全無法理解的。換句話說,杜尚這位當代藝術的鼻祖,是地地道道的現代藝術家,甚至是格林伯格意義上的“現代主義”藝術家。
如果說提出藝術唯名論是德·迪弗詮釋西方現代藝術史的最大的理論抱負,那么,重新解釋格林伯格就成了他打通現代主義與前衛藝術,或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的重大決策。一方面,通過對抽象繪畫史上的管裝顏料和空白畫布的梳理,德·迪弗得以重拾從抽象繪畫到現成品的藝術史上失落的鏈節(第三章);另一方面,通過對格林伯格現代主義理論及其晚年思想的細讀,他又能頗有說服力地論證格林伯格與杜尚殊途同歸的命運(第四章)。他似乎成功地將格林伯格的名言“一張繃緊的畫布已經是一幅畫,盡管不一定是一幅成功的畫”解釋為現代主義繪畫的邏輯結論就是現成品(一塊空白畫布),雖然那未必就是格林伯格本人的意思(考慮到格氏整個后半生都在反對一個人,那就是杜尚)。
不管怎么說,所有這一切都顯示了當代藝術是如何與現代藝術深深地交織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說,在現代藝術之外,根本沒有當代藝術這回事!假設我們不了解杜尚小便器所針對的那個現代藝術的機制(即從法國沙龍展,到落選者沙龍,再到獨立沙龍的創作、展覽、批評的機制),那么我們根本就不可能理解現成品的意義,也就不可能理解建立在現成品基礎之上的半數當代藝術作品。反觀國內的當代藝術生態,其危機性癥候最清楚地體現在“現代主義已死”、“形式主義死亡”、“格林伯格過時”之類的口號和臆想中。且不論上世紀90年代中國“后學”的意識形態之爭的背景,面對西方整整100年的現代藝術實踐和理論,種種急欲“后”之而后快的中國式后現代主義,即使到了2000年以后,依然是當代藝術擺脫不去的夢魘。
缺乏對西方現代藝術的深層機制的認識,人們也就只能唯西方最新潮流是瞻,不斷沉浮于歐美當代藝術層層泛起的浪花和泡沫中。美術界浮躁病皆由此而起:對西方現當代藝術的了解,基本上建立在新聞報道的水平。大量報道當代藝術展事的藝術新聞類雜志,不僅充斥著藝術家的工作室,而且也源源不斷地免費送往批評家和理論家的書房。真正有深度和厚度的研究,則幾乎絕跡。因此,德·迪弗所提供的視野,當如空谷足音,彌足珍貴。
比如,人們習慣于不假思索地照搬西方當代藝術的大量技術手段,卻不明白這些技術手段背后的全部思想肌理和藝術史背景。關于現成品的產生及其意義,《杜尚之后的康德》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注解。它既從理論上回答了現成品的藝術史意義問題(即所謂格林伯格與杜尚的合流問題,以及管裝顏料與空白畫布之為從抽象繪畫走向現成品,從特殊藝術走向一般藝術的鏈節問題),更從知識考古學的視點,發掘現成品作為唯名論藝術觀的范式的意義。對德·迪弗來說,要理解現成品的意義,借重于杜尚的精神后裔博伊斯的“人人都是藝術家”的口號(這是博伊斯對杜尚小便器的詮釋),只是一個方便之門。關鍵的解答還得追溯到18世紀以來的啟蒙現代性方案。這一方案在美學上的起點,當然是康德的《判斷力批判》。而康德第三《批判》一個秘而不宣的核心,就是宣布“人人都是鑒賞家”(所謂的“共通感”,或“共同感覺力”,正是這一點確保了鑒賞判斷的普遍可傳達性)。德·迪弗重點論述了,將藝術品交付于普通公眾裁決的平等意識——這就是法國沙龍藝術展,特別是落選者沙龍和獨立沙龍的理智地平線——才促使杜尚意識到“是觀眾創作了繪畫”……“人人都是藝術家”(杜尚差點說出這一點,但終究沒有說出,這也是博伊斯抱怨他的原因)。
如果說這就是德·迪弗對現成品的解釋,那么充其量他只是一個藝術理論家。我認為,《杜尚之后的康德》一書最有價值的地方,卻是表明作者還是一個卓越的藝術史家。因為正是德·迪弗,對杜尚如何撫摸秋季沙龍給他帶來的傷痛,如何倚重于其在美國的聲望,對紐約獨立藝術家大展的章程及其制度作出了巧妙的回應等等,作出了精僻的解讀。他對杜尚利用自我沉溺的藝術家埃爾希繆斯的心理刻畫,極具震撼力;而他對杜尚調用紐約前衛藝術代言人、攝影家斯蒂格勒茲的天才手法,充滿了既有批判,又有同情的理解。所有這些,都旨在說明《泉》作為劃時代的重大事件所富有的藝術史意義。可以說,不明了杜尚的現成品在反思和批判藝術現代性問題上的強有力的針對性,我們就不可能理解它的意義。
從杜尚將創傷性經驗升華為一種藝術行為,徹底改變了原有的藝術游戲規則,或者可以說,重新確立了藝術的游戲規則這一點著眼,德·迪弗的解釋給了我們諸多啟發。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人們往往會鬧出“瞎起哄”的笑話,這不能怪他們;要怪,也只能怪我們的藝術史家。正是他們放棄了起碼的崗位意識,一窩蜂地越俎代庖,要替藝術家們去尋找創作靈感。結果是,藝術史界永遠沉浮于追逐浪花的時髦之中。然而,德·迪弗的書卻使我意識到,如何將經驗升華為表達,既而上升為規則(如果你有足夠的智慧和幸運的話),是比任何時髦的藝術問題都更加重要的課題。假如不能從根本上來解決這一課題,我們就只能永遠成為西方當代藝術的膚淺的模仿者和幼稚的學習者。
上世紀80年代,美術界幾乎人人都在讀薩特和弗洛伊德;90年代初,大家又都沉溺于海德格爾和尼采;90年代下半葉,福柯和德里達成了時尚;2000年以來,熱門人物是德勒茲和鮑德里亞,最近則又轉向齊澤克和阿甘本……急于尋找創作靈感的藝術家們如此追逐明星般的哲學家,還情有可原。可怕的只是美術史界的熱點似乎也以此為轉移。好不容易介紹個把批評家和藝術理論家,不是阿瑟·丹托就是朗西埃,換句話說,還是哲學家。在這個語境里,德·迪弗的參照意義就變得清晰起來。僅就當代藝術理論的資源而言,德·迪弗所代表的康德路線,就構成黑格爾路線(例如阿瑟·丹托)的一個很好的平衡點。
當代藝術界是將阿瑟·丹托當作救世主來加以拱奉的。后者解放了他們,他的口號讓他們感到寬慰:“什么都行;沒有藝術品會跌出藝術史之外。”也就是說,你只要做就行了。至于做了什么,怎么做的,為什么要做等等,都無關宏旨。反正只要做了,就會被拍成照片,發表在藝術雜志甚至“藝術史”書籍里,換言之,你就進入歷史了!阿瑟·丹托的黑格爾主義藝術史模型是這樣的:先有一個瓦薩里敘事(藝術即再現),然后是一個格林伯格敘事(藝術即媒介),再后就是他老人家阿瑟·丹托的敘事(藝術即什么都可以)。在瓦薩里敘事里,凡是能夠精確再現的藝術才是藝術,否則就不是藝術;在格林伯格的敘事里,凡是符合藝術媒介本質的才是藝術,否則就不是藝術;而在藝術終結之后的“后藝術史時代”,已經不存在界定藝術品本質的可行辦法,因此“一切皆藝術”。
雖說德·迪弗的理論本身有時候也會帶有一絲黑格爾主義色彩(例如他關于理論界定義“藝術”一詞的種種可能的描述,詳見本書第一章),但總的來說,他的視野要比丹托開闊得多。具體來講,歐洲現代思想史(特別是啟蒙現代性思想和浪漫主義)就不是阿瑟·丹托所具備的知識面(這是由后者的哲學家身份,而非思想史家或藝術史家的身份決定的),因此,他對杜尚的解釋(很少涉及沃霍爾),就擁有一種阿瑟·丹托完全不可能擁有的思想厚度。
如果說沃霍爾是丹托所說的“一切皆可”的榜樣,那么,德·迪弗的英雄則是杜尚。更大的差異在于:當丹托欣快地宣布“藝術終結之后”的后藝術史的到來,在這個后藝術史階段,歷史終于擺脫了“只有一種藝術正確”的意識形態,終于來到了“什么都可以”的時代的時候,德·迪弗則在艱難地尋找藝術史上失落的鏈節,即從抽象繪畫到現成品,或從格林伯格到杜尚的過渡。更有甚者,兩者的心結大相徑庭:丹托“樂于”見證黑格爾藝術終結論(或哲學對藝術的剝奪;在他看來,沃霍爾的《布里洛盒子》便是哲學對藝術的剝奪的例證,而沃霍爾本人則是一位哲學家),而德·迪弗卻要為杜尚之后的康德美學的命運大傷腦筋(在他看來,杜尚的《泉》既是對康德美學的挑釁,更是對整個啟蒙現代性方案的挑戰)。麻煩在于,丹托不僅樂見藝術的終結,而且歡呼“后藝術史”的到來,他甚至認為,這還是人類的解放(因此落入啟蒙現代性的窠臼),而德·迪弗卻試圖在康德美學、杜尚的小便器與格林伯格的現代主義理論之間,找到一種合理的連續性說明,在必要的時候,“審美的法理學”也被用來增加藝術史的厚度和藝術判斷(或藝術批評)的重量。因此,在丹托的敘述輕易地從瓦薩里模型轉向格林伯格模型時,現代展覽制度(從沙龍到落選者沙龍再到獨立沙龍),及其在哲學中的反映(特別是康德的啟蒙現代性方案;不獨如此,更多德國浪漫主義的思想資源),完全不在丹托的視野內。這使得德·迪弗的現代藝術考古學不僅成為丹托的必要補充,甚至,更確切地說,成為后者的一個對反。
在現當代藝術理論中,人們爭論得最多的問題可能是:杜尚的小便器是不是藝術?如果是,正如概念主義藝術家科蘇斯所認為的那樣(藝術是概念并且只是概念),那么,現代藝術史上一定有一半作品要被排斥在外;如果不是,正如格林伯格所認為的那樣(藝術不是概念而是趣味對象),那么,現代藝術史同樣要有一半作品被排斥在外。這就是德·迪弗所說的現代藝術中的“二律背反”。為了解決這一二律背反,本書作者顯示了最杰出的思辨能力和最具原創性的思想見識(參見本書第五、六章)。
對傳統主義者或者甚至膚淺的現代主義者來說,杜尚的《泉》根本不是藝術,因此無需認真對待。在中國,公眾的興趣還普遍停留在古典趣味(少數人則徘徊在古典主義與現代主義之間),對他們來說,如此鄭重其事地研究一個臭名昭著的小便器,是不恰當的。可是,他們沒有意識到,《泉》已經過去了差不多100年。將它從藝術史上抹去,意味著要抹去近100年的藝術史上將近一半的藝術品!中國的美學家們反復告訴讀者,當代藝術是一堆垃圾。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美學研究基本上還囿于朱光潛和宗白華的視域。盡管有不少冠以《西方現代美學》或者甚至《當代美學》之類的著述問世,但你稍微留意一下,便可發現它們處理的多半是古典美學或一丁點兒現代美學的問題,根本沒有觸及美學現代性的真正核心;或者雖然涉及一些當代問題,但基本上是哲學(解構主義等)或文學理論(女性主義等)的翻版。20世紀以來,對哲學構成了最大挑戰的視覺前衛藝術,大體上仍落在國內美學研究的視野之外。杜尚的小便器曾使一切美學理論歸于無效,因此,一種不能直面杜尚的美學,根本就不是美學。
在這個語境里,《杜尚之后的康德》就顯示出完美的針對性來。嚴格地講,德·迪弗的這本書并不是一部美學著作,但它卻將作為一個學科的美學置于危急關頭。如果說杜尚的小便器構成了對康德美學的最大挑戰,那么,德·迪弗的這部書無疑就是對康德美學的某種捍衛:它的主旨倒不是杜尚之后如何延續康德美學的命題,例如如何維系美的對象與日常用品的視覺差異——如果是這些命題,那他就與丹托重疊了,或者至少無法超越丹托了——而是如何在杜尚的小便器之后重構康德美學,從而使它擔當起發掘整個藝術現代性的考古學的使命。
這一使命集中地體現在德·迪弗關于藝術的唯名論的理論建構中。在他看來,在西方現代藝術中,“藝術”并不是一個普通名詞,而是一個專名(參照約翰-斯圖爾特·穆勒/伯特蘭·羅素/弗雷格/克里普克那個哲學譜系中的專名理論)。也就是說,現代藝術是以作為專名的藝術為調節性理念的。“藝術”在西方現代藝術中,只有指稱,沒有意義。換言之,這個詞在西方現代社會,并沒有邏輯學家所說的確定內涵,也沒有符號學家所說的普遍意義。因此包括人類學家和藝術史家在內的邏輯本體論者,或者包括社會學家或批評家在內的符號學家,對此沒有發言權。那么,誰有發言權呢?德·迪弗認為,從18世紀法國沙龍展開始,這個有發言權的人就是藝術的業余愛好者。
在這個過程中,德·迪弗寫出了全書最漂亮的章節之一,在我看來,這是對藝術本質問題的理論史的最好概括(參見本書第一章)。請讀者留意這一章的幾個注釋,特別是簡要概括(主要是)德語藝術史學的注釋5,以及扼要描述前衛的藝術史家的注釋10。在前一個注釋里,作者提到了溫克爾曼、李格爾、沃爾夫林、德沃夏克、潘諾夫斯基、熱爾曼·巴贊、里奧奈羅·文杜利、喬治·庫布勒、漢斯·席德邁爾和貢布里希。在后一個注釋里,作者談及羅亞爾·柯提索斯、羅杰·弗萊、希爾頓·克萊默、本雅明·布赫洛、阿諾德·豪澤爾、安塔爾、尼柯斯·哈津尼可勞、奧爾特加·加塞特、赫伯特·里德、T. J. 克拉克以及彼得·比格爾。當然,作者還少量涉及一些分析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符號學家的著作。單單這份名單,就足以發現本書在討論當代藝術問題上的視野,也可以一窺中文藝術史學界的欠缺。文獻的不足總是學術研究最大的困擾。前一個注釋提到的德語藝術史家,我們還較為熟悉(范景中先生及其團隊對此貢獻甚大),但對后面那個注釋提及的文獻,除個別例外,國內的研究總的來說才剛剛開始(只有包括本人在內的少數學者在這個領域工作)。
十多年前我在英國訪學時,這本書出版不久,我躬逢其盛,急切地拜讀過。數年前,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的詹姆斯·艾爾金斯教授再次向我推薦此書,認為它“對某些藝術概念的梳理,是任何討論當代藝術的人不可忽略的”。雖然,正如作者在“致謝”里已經指出過的,這本書的第一、五、六章曾以《藝術之名》出版過(法文版),而且已經有過中譯本,但是,僅有這三章遠遠不足以全面理解作者的核心思想。更何況作者也已指出,收入到本書后,這些章節已作過徹底重寫。因此,我們將全書翻譯出來,供國內對當代藝術理論感興趣的讀者參考。
翻譯的分工是這樣的:沈語冰翻譯了第一、二、五、六章;張曉劍翻譯了第三、四章;陶錚翻譯了第七、八章。最后由沈語冰通讀了全書。
中國當代藝術似乎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當代藝術的實踐、理論和批評中都還存在著諸多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對西方現當代藝術史論與批評了解得不夠。這一點既有語言障礙造成隔閡的原因,也是史論家放棄崗位意識、急于想要為藝術家尋找“最新思想”所致。每當國內的藝術家/策展人/批評家/藝術史家——在中國諸多身份經常是不分的——這是前現代性的征兆,還是中國式后現代主義的寫照?——急于將西方的最新思潮“空降到”當代藝術現場,或者,每當有人大發當代藝術與中國文藝復興的宏論時,我就感到事情不妙。因為我們距離真正意義上討論當代藝術,特別是與歐美同行討論當代藝術,還相當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