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把粗木椅子,坐墊是草扎的,屋里雖簡陋,椅腿卻可舒暢地伸展,那是爺爺坐過的吧!或者它就是老爺爺!椅上一只煙斗透露了咱們家生活的許多側面!椅腿椅背是平凡的橫與直的結構,草墊也是直線向心的線組織。你再觀察吧,那樸素色彩間卻變化多端,甚至可說是華麗動人!凡是體驗過、留意過苦難生活、純樸生活的人們,看到這畫當會感到分外親切,它令人戀念,落淚!
凡·高熱愛土地,他的大師風景畫不是景致,不是旅行游記,是人們生活在其間的大地,是孕育生命的空間.,是母親!他給弟弟提奧的信寫道:"……如果要生長,必須埋到土地里去。我告訴你,將你種到德朗特的土地里去,你將于此發芽,別在人行道上枯萎了。你將會對我說,有在城市中生長的草木,但你是麥子,你的位置是在麥田里……"他畫鋪滿莊稼的田野、枝葉繁茂的果園、赤日當空下大地的熱浪、風中的飛鳥……,他的畫面所有的用筆都有運動傾向,表示一切生命都在滾動,從天際的云到田壟的溝,從人家到籬笆,從麥穗到野花,都互相在呼喚,在招手,甚至天在轉,地在搖,都緣畫家的心在燃燒。
凡·高幾乎不用平涂手法。他的人像的背景即使是一片單純的色調,也憑其強烈韻律感的筆觸推進變化極微妙的色彩組成。就像是流水的河面,其間還有暗流和游渦。人們經常被他的畫意帶進繁星閃爍的天空、瀑布奔騰的山谷……他不用純灰色,但他的鮮明色彩并不艷,是含灰性質的、沉著的。他的畫面往往通體透明無渣滓,如用銀光閃閃的色彩所畫的西萊尼飯店,明度和色相的掌握十分嚴謹,深色和重色的運用可說惜墨如金。他善于在極復雜極豐富的色塊、色線和色點的交響樂中托出對象單純的本質神貌。
無數杰出的畫家令我敬佩,如周方、郭熙、吳鎮、仇英、提香、柯羅、馬奈、塞尚……我愛他們的作品,但并無太多要求去調查他們繪畫以外的事。可是對另外一批畫家,如老蓮、石濤、八大、波提切利、德拉克羅瓦、凡·高……我總懷著強烈的欲望想了解他們的血肉生活,鉆入他們的內心去,特別是對凡·高,我愿聽到他每天的呼吸!
文森特·凡·高1853年3月30日誕生于荷蘭格魯脫·尚特脫。那里天空低沉,平原上布著筆直的運河。他的家是鄉村里一座有許多窗戶的古老房子。父親是牧師,家庭經濟并不寬裕。少年文森特并不循規蹈矩,氣質與周圍的人不同,顯得孤立。唯一與他感情融洽的是弟弟提奧。他不漂亮,當地人們老用好奇的眼光盯他,他回避。他的妹妹描述道:"他并不修長,偏橫寬,因常低頭的壞習慣而背微駝,棕紅的頭發剪得短短地,草帽遮著有些奇異的臉。這不是青年人的臉,額上各現皺紋,總是沉思而鎖眉,深深的小眼睛似乎時藍時綠。內心不易被信識,外表又不可愛,有幾分像怪人。"
他父母為這性格孤僻的長子的前途預感到憂慮。由叔父介紹,凡·高被安頓到巴黎畫商古比在海牙開設的分店中。商品是巴黎沙龍口味的油畫及一些石版畫,他包裝和拆開畫和書手腳很靈巧,出色地工作了三年。后來他被派到倫敦分店,利用周末也作畫消遣,他那時喜歡的作品大都是由于畫的主題,滿足于一些圖像,而自己的藝術靈感尚在沉睡中。他愛上了房東寡婦的女兒,人家捉弄他,最后才告訴他,她早已訂婚了。(具體的戀愛過程恐怕誰也說不清楚,所以不要輕信任何一種說法-館長注)他因而神經衰弱,在倫敦被辭退。靠朋友幫助,總算又在巴黎總店找到了工作。他批評主顧選畫的眼光和口味,主顧可不原應諒這荷蘭鄉下人的勸告。他并說:"商業是有組織的偷竊。"老板們很憤怒。此后他來往于巴黎、倫敦之間,職業使他厭倦,巴黎使他不感興趣,他讀圣經,徹底脫離了古比畫店,其時二十三歲。
他到倫郭教法文,二十來個學生大都是營養不良面色蒼白的兒童,窮苦的家長又都交不起學費。他改而從事宣道的職業,感到最迫切的事是寬慰世上受苦的人們,他決心要當牧師了。于是必須研究大學課程,首先要補文化基礎課,他寄住到阿姆斯特丹當海軍上將的叔父家里,頑強地鉆研了十四個月。終于為學不成希臘文而失望,放棄了考試,決心以自己的方式傳道。他離開阿姆斯特丹,到布魯塞爾的福音學校。經三個月,人們不能給他明確的任務,但同意他可以自由身份冒著危險去礦區講演。他在蒙斯一帶的礦區工作了六個月;仿照最早基督徒的生活,將自己所有的一切分給窮苦的人們,自己只穿一件舊軍裝外衣,襯衣是自己用包裹布做的,鞋呢?腳本身就是鞋。住處是個窩,直接睡在地上。他看護從礦里回來的工人,他們在地下勞動了十二小時后精疲力竭,或帶著爆炸的傷殘。他參與斑疹傷寒傳染病院的工作。他宣教,但缺乏口才。他瘦下去,朋友趕來安慰他,安排他住到一家面包店里。委以宗教任務的上司被他那種過度的熱忱嚇怕了,找個借口撤了他的職。
他宣稱:"基督是最最偉大的藝術家。"他開始繪畫,作了大量水彩和素描,都是礦工生活。宗教傾向和藝術傾向間展開了難以協調的斗爭,經過多少波濤的翻騰,后者終于獲勝了!他再度回到已移居艾登的父親家,但接著又返回礦區去,赤腳流血,奔走在大路的贖罪者與流浪者之間,露宿于星星之下,遭受"絕望"的蹂躪!
凡·高已二十八歲,他到布魯塞爾和海牙研博物館里去看大師們的作品。使他感興趣的不再是宗教的或傳說故事的圖畫,他在倫勃朗的作品前停留很久很久,他奔向了藝術大道。然而不幸的情網又兩次摧毀了他的安寧,一次是由于在父母家遇到了一位表姐;另一次,1882年初,他收留了一位被窮困損傷了道德和肉體的婦人及其孩子,和她一起生活了十八個月。凡·高用她當模特,她飽酒,抽雪茄,而他自己卻常挨餓。一幅素描,畫她絕望地蹲著,乳房萎垂。凡·高在上面寫了米歇勒(1798--1874年,法歷史學家和文學家)的一句話: "世間如何只有一個被遺棄的婦人!"

凡·高終于不停地繪畫了,他用陰暗不透明色彩畫深遠的天空,遼闊的土地,故鄉低矮的房,當時杜米埃對他起了極大的影響,因后者幽暗的低音調及所刻畫的人與社會的面貌對他是親切的。《吃土豆的人們》便是此時期的代表作。此后他以巨人的步伐高速前進,他只有六年可活了!他進了比利時的盎凡爾斯美術學院,顏料在他畫布上泛濫,直流到地上。教授吃驚地問:"你是誰?"他對著吼起來:"荷蘭人文森特!"他即時被降到了素描班。他愛上了魯本斯的畫和日本浮世繪,在這樣的影響下,解放了的陰暗色調,他的調色板亮起來了。也由于研究了日本的線描富岳百圖,他的線條也更準確、有力、風格化了。
他很快就不滿足于盎凡爾斯了,1886年他決定到巴黎與弟弟提奧一同生活。以前他幾乎只知道荷蘭大師,至于法國畫家,只知米勒、杜米埃、巴比松派及蒙底塞利,現在他看德拉克羅瓦,看印象派繪畫,并直接認識了洛特來克、畢沙羅、塞尚、雷諾阿、西斯萊及西涅克等新人,他受到了光、色和新技法的啟示,修拉特別對他有影響。他用新眼光觀察了。他很快離開了谷蒙的工作室,到大街上作畫,到巴黎。巴黎解放了他的官感情欲,是《輪轉中的囚徒》一畫喚起他往日的情思。
然而他決定要離開巴黎了!經濟的原因之外,他主要不能停留在印派畫家們所追求的事物表面上,他不陶醉于光的幻變,他要投奔太陽。一天,在提奧桌上寫下了惜別之言后,西方的夸父上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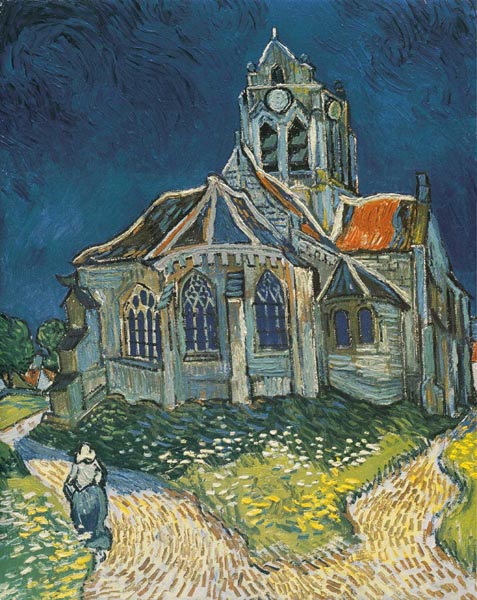
1888年,凡·高到了阿爾,在一家小旅店里租了一間房,下面是咖啡店。這里我們是熟悉的:狹的床和兩把草椅、咖啡店的球臺和懸掛著三只太陽似的燈。他整日無休止地畫起來:床與街道、公園、落日、火車在遠景中穿行田野、花朵齊放的庭院、罐中的自畫像……他畫,畫,多少不朽的作品在這短短的歲月源源誕生了!是可歌可泣的心靈的結晶,絕非尋常的圖畫!
他贊美南國的阿爾:"呵!盛夏美麗的太陽!它敲打著腦袋定將令人發瘋。"他用黃色涂滿墻壁,飾以六幅向日葵,他想在此創建"友人之家"。邀請畫家們來共同創作。但應邀前來的只高更一人。他倆熱烈討論藝術問題,高更高傲的訓人口吻使凡·高不能容忍,凡·高將一只玻璃杯扔向高更的腦袋,第二天又用剃刀威脅他。結果凡·高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高更急匆匆離開了阿爾,凡·高進了瘋人院。包著耳朵的自畫像、病院室內等奇異美麗的作品誕生了!他的病情時好時壞,不穩定,便又轉到數里以外的圣·來米的瘋人收容所。在這里他畫周圍的一切:房屋與院、橄欖和杉樹、醫生和園丁……熟透了的作品,像鮮血,隨著急迫的呼吸,從割裂了的血管中陣陣噴射出來!
終于,《法蘭西水星報》發表了一篇頗理解他繪畫的文章。而且提奧報告了一個難以相信的消息:凡·高的一幅畫賣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