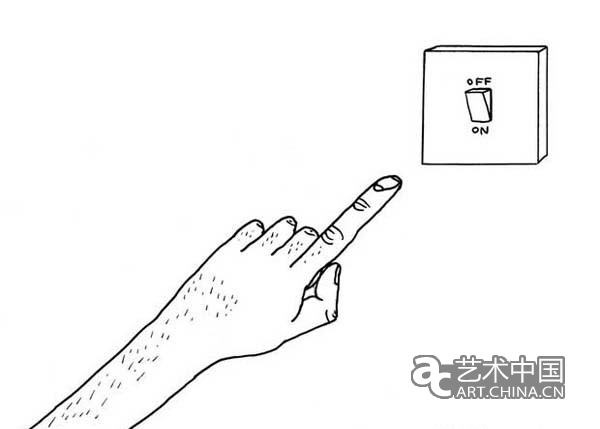
David Shrigley 的動畫作品《Lightswitch》截圖
作為世界當代藝術的重要獎項,2013年在爭議中迎來了特納獎的第29個年頭。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的特納獎不僅首次在北愛爾蘭舉辦展覽和頒獎儀式,并且破天荒地提名一位黑人藝術家Lynette Yiadom-Boakye和一位創造非物質材料的藝術家Tino Sehgal,無疑又給獎項添了亮點,而另一位提名者David Shrigley則把英國人的冷幽默發揮到了極致。最終,Laure Prouvost憑借她的影像裝置斬獲大獎,并獲得近41000美元的獎金。評委評價她的作品“以一種完全當代的方式使用了電影,把觀眾帶入到內心世界,并參考了后互聯網時代的圖像流變”。大喜過望的法國藝術家上臺領獎時卻說:“有其他3位這么棒的提名者,我一直確信絕不會是我(得獎)。”
“先鋒與反叛”自始至終都是成就“特納獎”的不二法門,一方面為觀眾掙脫藝術想象力的桎梏提供了一個支點;另一方面,其“爭議性”也使特納獎在叫好與唾沫的論戰中備受關注。于是,人們似乎已經達成了一種心照不宣的共識,即對于特納獎來說:不先鋒,不反叛,則不藝術。2013年的特納獎也不乏反叛精神,藝術家David Shrigley跟觀眾開著無底線的玩笑,而Tino Sehgal更為大膽,直截了當地反對任何物質材料。按特納獎一貫的邏輯,最具挑釁性和原創性的Sehgal理應獲獎,而最終結果多少讓人感到意外。
特納獎獲得者Laure Prouvost以其層次豐富的故事和具有超現實瞬間的影像裝置為人所知,此次獲得提名的作品是《Wantee》和《Far from words》。《Wantee》在一個昏暗的房間中展示,其中擺滿虛構的藝術家祖父自制的茶壺、拼貼畫和雕塑。作品名字來源于達達藝術家Kurt Schwitters的女友,因為她經常問Schwitters“want tea?(想喝茶嗎?)”。而在影像裝置作品《Far from words》中,空間的墻面布滿繪畫拼貼,其中有動物、植物和身體的圖像,也穿插著嵌入墻面的影像。這些影像運用蒙太奇手法,把呼吸聲、在森林中穿梭的身體,以及動物和自然的常態迅速地剪輯在一起,圖像與聲音有節奏地往復閃現,帶給觀眾一種超現實的穿越感。Prouvost認為電影可以喚起人的全部感官,包括嗅覺,她具有女性的敏感和直覺,能夠通過聲音、圖像之間的簡單嫁接,給予觀眾一種生理上的觸動,這或許正是她獲獎的原因所在。

David Shrigley 的作品《I'm Dead》
另一位被提名者David Shrigley的作品則展現出英國紳士機智且冷幽默的一面,一只小狗的標本舉著“我死了(I’m dead)”的牌子站在展廳中,既可愛又詼諧,似乎在提醒我們終將死去的現實。動畫作品《Lightswitch》是用一根手指反復撥弄著燈的開關,屏幕也隨之一亮一暗,頗有向2001年特納獎得主Martin Creed致敬的意思(Creed的獲獎作品《Work No.227》,即是展廳中忽明忽滅的燈)。Shrigley擅于在簡單的日常生活中獲取靈感,這些靈光乍現的點子有時能博人一笑,有時發人深思,有時也無異于網絡惡搞,這是當代藝術嗎?不管怎樣,Shrigley就像是這個乏味的時代的精靈,不時抖出個巧妙的包袱,不動聲色,簡練、機智、詼諧,又帶點低俗。
作為近年為數不多的被提名的畫家,Lynette Yiadom-Boakye是首位獲特納獎提名的黑人藝術家。她在深色背景下描繪黑人,白色的眼睛在背景下顯得相當突兀,畫面中經常出現拿著長槍的同胞,性別也時常曖昧不清。于是,人們不難給她貼上種族主義和女性主義的標簽,可以說,這種價值取向無可爭議地為她在西方語境中贏得了某種先鋒派立場。Yiadom-Boakye被提名倒更像是評委會的權衡之策,試圖以此重申架上繪畫——尤其肖像畫——在當代藝術中的話語活力。因為就作品本身而言,她對于繪畫語言的創造力,實在難以讓人印象深刻。
Tino Sehgal一直是2013年特納獎的最大熱門,結果公布前,不少英國的媒體都預測Sehgal會贏。短短幾年內,他參加了第13屆卡塞爾文獻展,在英國泰特美術館舉辦展覽,并且獲得了象征藝術界最高榮譽之一的威尼斯雙年展金獅獎。這位經濟系畢業的藝術家橫空出世,著實讓整個藝術圈倒吸了一口冷氣。更有意思的是,關于他的作品,人們甚至找不到任何官方的文字和圖像記錄,展覽圖錄中留給他的一頁,永遠是一張連頁碼都沒有的黑紙。
Tino以其反對物質材料著稱,在本次展覽的作品《This Exchange(這個交換)》中,“聊天”成了藝術。作品發生在一間光禿禿的白色空間中,觀眾被邀請進入對話,與表演者們談論對自由市場和交換的看法,觀眾會談到市場經濟、失業率等當地人所面臨的社會問題,而作為交換,觀眾可以獲得2英鎊的報酬。這些談話像一個巨大旋渦,把觀眾拽入到個人經驗之中,這些經驗會不自覺地提醒我們重新檢視自己,重新思考對交換的看法,莫名其妙的2英鎊酬勞更讓觀眾們不知所措:應該接受這2英鎊嗎?這次與表演者的交流是基于一次觀展經歷,還是一種為獲得報酬而進行的勞動?
Tino不愿用表演或行為藝術來定義他的創作,他認為他的工作是把人與人間的關系作為一種創作所使用的材料。而關于拒絕物質記錄,與其說是完整Tino藝術觀念的必要途徑,毋寧說是一個機智的噱頭,憑借這個噱頭,他的作品反而在大量的媒體描述與口口相傳中獲得了另一層含義。如他自己所言,對他作品的收藏,就是收藏一段記憶。即便如此,他的作品依然價格不菲,一件意圖反美術館體系的作品反而被美術館天價收藏,這不得不說是對現行藝術制度的莫大諷刺。

Laure Prouvost 的裝置作品《Wantee》現場
2013年特納獎既沒有授予另類幽默的David Shrigley,更沒像多數人預測的那樣頒給Tino Sehgal,這多少讓Tino迷們有些失望。想來Tino落選也在情理之中,如此風頭正勁的藝術家已經不需要再多一頂帽子了,況且若他當真獲獎,評委會也不免有些形同虛設的味道。話雖如此,獲獎者Prouvost的作品總歸與人們心中的特納獎印象有些出入,似乎少了點凌人的銳氣,倒多了點堂堂正正的中庸。作為一個老牌藝術大獎,特納獎既不想毫無懸念地上演眾望所歸,又不想輕易地落入俗套,著實是個兩難的抉擇,而最終的結果,只能說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吧。